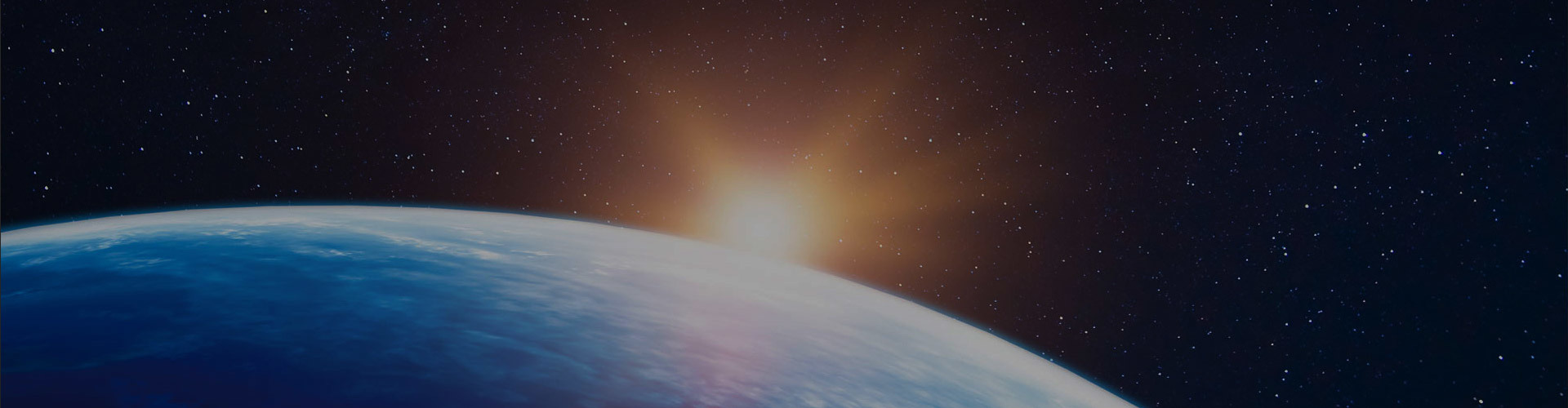04
2024
-
13
宁肯小说集《城与年》推出:面对城市记忆我有巨大的好奇和紧迫感
时间: 2024-04-13 23:28:12 | 作者: 华体会安卓版
近期,宁肯中短篇小说集《城与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集是这位生于1950年代末,在北京南城胡同里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作家对往昔的文学化追忆与重构。《火车》《黑雀儿》等篇章,展现了人性的荒寒;《探照灯》《防空洞》等篇章,有着对于孩童掌握权力之后人格扭曲的观照;通过《十二本书》《黑梦》,表现了孩童对于知识的渴求;通过《他挂在城墙上》《蓝牡丹》等篇章,表现了人性的悲悯;《九月十三日》表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个中人物命运的诡异。《城与年》不仅展现了作者童年记忆中的北京市井风貌,也揭示了人性的成长轨迹。在此前接受本报访谈时,惯于写长篇小说的宁肯表示,如果说长篇小说是文学的大陆、高原、高峰,短篇小说的难度则在于体积小,角面多,如熠熠闪光的钻石。但不管是写长篇、短篇,还是写非虚构作品,作家写作的意义都在于,是否给这样一个世界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傅小平:在我的印象中,你几乎是一个长篇小说家。偶然看到《火车》入选一些排行榜,我才知道原来这几年你还写起了短篇。后来你又陆陆续续写了《探照灯》等。近期,这些中短篇小说终于结集成《城与年》出版,我们就索性由此谈起。你在不算短的写作生涯里怎么就不寻常路,直接跳过中短篇的写作训练,径直奔长篇小说去了?
宁 肯:怎么说呢,我原来确实是不写短篇的。但写完五部长篇后,很想写写早年的生活,很多作家都写童年、少年时期的经历,我是写作到今天也很少用到早年的生活积累。我在北京出生、长大,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北京,也很少写北京,《沉默之门》里算是涉及一小部分,那也是写的特殊年代,不能算是真正写了。所以,我一直想写写早年,尤其是在这几个长篇写完以后。但我写早年生活至少有两个障碍,一是,我生活在文革或后文革时期,我老觉得没什么好写。你可能对那个年代没什么印象,那时物质、精神生活都极度贫乏,处于沙漠状态。我能想到的只是备战备荒、阶级斗争这类事情,还有语录、等等,都是一些符号化的东西,我很难还原到生动的现场里去。
傅小平:这可能还和你一直在城市里长大,并没过上山下乡的经验有关。写那个年代的小说里,似乎那些写到乡村或小镇背景的,要丰富生动一些。而且涉及那个年代,纯粹写城市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
宁 肯:对,写那个年代的乡村要好一些,乡村里除了我说的这些符号外,还有非常原生态的东西,像河流、村庄、邻里,等等。城市本身就特别格式化,我们那时候无非是在家庭、学校、单位这一些地方转来转去,所有的生活,几乎都可以纳入政治框架。所以,写这段生活应该写什么,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障碍,这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一直在写长篇,很少涉及早年生活,也就更难以处理那段时间。
宁 肯:第二个障碍与第一个障碍相关,就是“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小说要反映现实,反应已发生的,那么这个现实全是政治,又没什么可写,于是进入怪圈。事实上,小说更该写的是有几率发生的,如果是有几率发生的,那个年代反倒很特殊,有可独创性的空间。现实高度文本化,在这高度文本化的现实之上再创造一个文体非常难,但一旦创造出来就很独特。但一直以来我没意识到这点,反而形成了障碍。
傅小平:也就是说,你这些年意识到这点,也感觉自己写早年生活,能写出独创性了。当然也有一定的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你就想着“追忆似水年华”了。
宁 肯:随年纪增长,眼看着老北京在一天天消失,尤其是慢慢的变多老房子都看不到了,我就有紧迫感。我就觉得,童年生活再贫乏,你要是深入挖掘,也应该是有东西可写的。你哪怕生活在监狱里,随着回忆深入扩展,你也能有东西写。所以,我现在想回过头写了,但说实话,非常难。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做了一些准备。我先写了回忆性散文集《北京:城与年》,我就跟考古一样追溯早年生活,从我出生,到开始有记忆,然后是童年、少年,这么一直写下来,第一篇就叫《记忆之鸟》。
傅小平:单看这个题目,就能感觉到里面隐含了一种回溯的视角,还有一种俯瞰的视角。
宁 肯:反正我是从头开始,用最真实的记忆的方式捋一遍,看看自己能回忆起多少。刚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可写,甚至是觉得没什么,但一旦往记忆深处写,就像排雷似的,排完这一个,“啪”一声又慢慢的出现一片,原来我根本没意识到的东西浮现了。就这么着,我把很多记忆都给写出来了。
傅小平:还真是,你说的记忆,对应的就是“城与年”里的“年”啊。里面的“城”呢,大概就指的北京城了,我注意到你的微博、微信等题签都写的“城与年”,想来在强调一种时空观的同时,这个题签还代表了一些什么。
宁 肯:对,我只是用了一个比较文学化的说法。“城”对应空间,“年”对应时间,“城与年”也就是讲的空间与时间。这里还有一个缘由,苏联有个叫费定的作家,写过一部小说就叫《城与年》。
傅小平:是嘛?我还认为自身对苏俄文学算得上是比较熟悉的,但这部小说我之前都没听说过。
宁 肯:现在不怎么提了,所以你不知道。我从《十月》调到北京作协,编审本来可以转过来当一级作家,但要经过申报、答辩程序。答辩评委里就有刘庆邦、孙郁和周晓枫,答辨时我提到正在写的系列小说《城与年》,孙郁就说苏联的费定写了《城与年》,我说就是啊,我起这书名就受了他启发啊。他就说这个挺好。还有一个叫李林荣的评委说,你这个书名用在北京是最合适的,也就北京,我们都叫它北京城。我们不会管上海叫上海城,南京还可以叫南京城。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概念,北京城是有历史的,这里头有我成长、经历的印记。
傅小平:读《火车》的时候,我还疑惑里面是不是记录了你真实的成长经历。你写得逼真么,我读着有身临其境之感。尤其是开头:“一九七二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我们院几个孩子走在镜头中。”代入感真是挺强的,而且这般叙述本身就带有镜头感,你又写了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随后你又写道“安东尼奥尼并没特别对准他们,只是把他们作为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背景。”人并不包称也就从“我们”变成了“他们”,而这个“我们”也包括叙述者“我”,但你后来又把人称又从“他们”转换回“我们”。你是有意识地转换人称吗?
宁 肯:我觉得这既是有意的也是自然的转换,当一个人回忆许多年前自己和一帮孩子的往事,自然就会用到“我”和“我们”这样的视角,同时这“我”和“我们”因为遥远也变成客体,即“他们”,也就是说可完全当成为“他者”来回忆,一种天然的有心理依据的陌生化。
傅小平:这般镜头切换让人觉得小说后面发生的故事源自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画面,同时给人以大历史和小事件融汇到一起的印象。你是怎么想到的?
宁 肯:我最开始写,没这个想法。我本来想独立写安东尼奥尼拍《中国》这个事,这在当年是特别大的一个事。你想,尼克松访华,相当于打破了禁忌,过了没多久,这个意大利人就到中国来了,还拍摄首都北京。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这个事给我印象就特别深。当然,他拍的纪录片很快被批判,被打入冷宫。但这个事本身已经让我们震惊了,那时大家都会想,上层怎么会同意他来?单单是同意就有问题啊。更何况,他这一个名字当时听起来也特别古怪。但写《火车》的时候,我就想到可以把这个事给放进去。《中国》是一部很长的纪录片,里面有火车的镜头,我不是在小说里写那帮孩子到火车站玩么,我就想这样的镜头有可能被拍下来,我也是写的那个年代的事,时代感就有了。
傅小平:小说里小伙伴们一起搭火车,“我们”从上面跳下来了,但那个女孩子却没跳下来。这里面是不是隐含了什么?我这么问是因为,类似火车,尤其是行进中的火车这样的意象,常常被人理解为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的隐喻。
宁 肯:其实在写作的人看来,他写的时候往往没想那么多,主要就是一种感觉。这个小说里有些片段吧,我在那本《北京:城与年》也写了。我们小时候老从琉璃厂出发,到永定门看火车,铁道上还有化石一样的东西,我们拿回在马路上面写字。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事情,我就写在里头了。还有一个记忆,那时我已经上中学,应该是一九七五年吧,我们学工劳动,在北京青年湖那边砌一个啥东西,那旁边是一个货场,里面就停了好多火车。我们大家常常过去玩,尤其到火车车尾上玩。这些印象综合到一起,也就有了这样的构思。
傅小平:读过《北京:城与年》里部分章节,对其中《探照灯》那篇印象比较深,你现在又写了同题小说,可见两者之间有关联。你在小说里细节还原这么逼真,也应该有你先写了散文的缘故。是不是你写散文时就有了写短篇的考虑?
宁 肯:我写这些散文就是为写小说的,我是觉得那里面有些可以写成小说,所以写它们也是写小说前的一种准备吧。我还在微博上自嘲了一番:我说我这么想自己都觉得很天真,散文毕竟和小说区别很大,这不太可能嘛,要是可能大家不这么干?先写一本散文再在此基础上写一部小?有点天方夜谭味道。
傅小平:不过对你来说,我觉得不成问题。我是基于对你小说的阅读,而不是知道你写了短篇才这么说的。你的小说,尤其是你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我读的时候就觉得和你写的散文有一些相通之处。以我的阅读,像《蒙面之城》《天·藏》可以说是诗化的小说,更准确地讲是散文化的小说。我读里面有些段落还有一种错觉,你会不会是先写了散文的片段,然后再组合到小说里去的。
宁 肯:那倒没有。在写《蒙面之城》之前,是一九八六年吧,我是写过两篇散文《天湖》和《藏歌》的,但这和我写小说没什么关系。散文呢,又太杂,你要想写散文写出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那时写散文是怎么一个背景呢,就是八十年代,我们对朦胧诗派,还有先锋小说这两个思潮知道比较多,实际上当时还有个“新散文”写作的思潮。但散文很杂,它无所不包啊,它看似有话语霸权,但范围太广,很难聚焦,也就很难有定论,所以这个思潮现在不怎么被提了。但要从散文流派角度,“新散文”写作绝对可以称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流派。
傅小平:还真是,我对这个流派没什么印象。在我印象里,新时期以来,能称得上流派的大概也就所谓大文化散文。我约略也知道贾平凹倡导的美文写作,因为亲历和见证,对在场主义散文知道,但这些也不算流派。大概散文难以归类,也就很少有流派的说法。不过你在《说吧,西藏》序里提到的在场视角、开放姿态,以及把散文当成创造性的文本经营等观点,读后确实有启发。倒是有些好奇,这是你后来做的反思,还是当时对这一流派所做的经验总结?
宁 肯:“新散文”概念正式提出是1998年《大家》设立了“新散文”栏目,1999年《散文选刊》推出“新散文作品选”。按语称:“作为一门古老手艺的革新分子,新散文的写作者们一开始就对传统散文的合法性(目的性)产生了怀疑:它主要是表意和抒情的功能、它对所谓意义深度的谄媚,无不被放置在一种温和而不失严厉的目光的审视之下。”很显然“新散文”栏目的设置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看到自八十年代以来一批散文写作者贡献了不同于传统的散文的一个命名。我的序的总结也是在其后反思自己八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做出的,其时已到了2004年。
傅小平:你早年写的散文,应该说比较多实践了你在这篇序里提到的理念。但你后期写的散文却给我感觉,似乎更多回归传统的路子上去了。
宁 肯:我在我的散文集《我的二十世纪》的序言《审美散文与工具散文》一文大概回答了你的问题:在我看来,散文就两种,一个是工具散文,一个是审美散文。工具散文有审美性,审美散文有工具性。这是我对散文基本的分类或看法。我虽然写了一些审美散文,但就数量而言更多还是工具散文,仅就我自己而言,审美散文的写作缺乏技术性,倒是工具散文慢慢的变多地伴随自己。工具散文是散文的常态、大树、主河,审美散文(“新散文”)不过是支流,是散文大世界的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品种,其未来就像其本身一样是不确定的。
傅小平:我注意到你把部分创作谈、对话等也纳入散文集里。你长于文体实验么,不妨说说怎么看这两种文体?我有个大体印象,近些年作家们挺能写创作谈的,他们在访谈中也通常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但要由此对照他们的创作,却多少有些落差。我偶尔也会感慨一下:相比写小说,现在作家分明更擅长谈小说么。
宁 肯:你说得不错,我也感觉到了。我想可能和推广作品有关,一个东西发出来,选刊选了,或媒体宣传,创作谈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催生创作谈的繁荣。其实创作谈和创作完全是两回事,作家的话,我是说创作谈往往不可信。
一九七二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我们院几个孩子走在镜头中。安东尼奥尼并没特别对准他们,只是把他们作为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背景,车上挤满蓝色人群,我们院的孩子只停留了十几秒钟便走出画面,向城外走去。城墙已经消失了,护城河还在,过河就是城外:铁路,庄稼地,二道河与三道河。二道河是污水,河汊纵横如车辙,那是我们院孩子抵达最远的地方。听说过三道河没去过,通常就在铁道边上玩。从后来才见到的片子看,他们是五一子、大鼻净、小永、大烟儿、文庆、小芹。小芹是唯一的女孩,但是跟男孩差不多,一个颜色。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谁呢?他比别人都矮了一大截,落得有点远,而且不像是和前面一伙的。但没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四十年后我在镜子中看到他,他也老了。别以为侏儒不会老,照样会老,满头银发雪山似的,照耀着短小的藕节似的身体。
他们——当然也可说我们——过了桥。桥是南城的永定门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要不是简易栏杆几乎看不出是座桥,路面也是一样的柏油与反光。桥上永远有人在打鱼,冬天凿开冰也打,每天打得上来打不上来都打,网抬起落下,像钟一样准确。总有含着长烟袋一动不动的老人围观,就是说不管这个城市已走了多少人总有闲人。街上也还有人,公共汽车空荡荡,但算不上空驶。偶尔车后面跟着辆自行车,汽车多快自行车就多快,没任何原因。阳光不错,路面反光,汽车、人、自行车像在镜子中。
护城河泾渭分明映着城市、农村、环城铁路,火车慢慢悠悠,汽笛声声,大团的白雾飘过河来,被坚硬的城市吸尽。白雾在田野上要飘很久,这也是我们喜欢河对岸的原因之一。我们在铁路上奔跑,追着白雾。铁路本是麻雀的世界,麻雀起起落落,重复飞翔。我们的奔跑没有重复感,我们只是几个孩子,并且奔跑的原因不明,与食物无关。枕木的节奏决定着我们的奔跑,只要踏上枕木不跑不行,直到有人带头卧下才全都卧下。没人教我们倾听,只是一人俯耳大家就都跟着——好多事都这样,然后竟真的听到了轻轻的震动。尽管就课本而言我们是白痴,但本能异常聪明。火车来了,尽管在远方,但是来了,远远的来了,简直有音准。虽然我们不知道音准但已听出来,声音慢慢的升高,越来越密,越来越响,然后我们一哄而散……
黑色的火车红色的曲臂,喷着热气一下将我们吞没,什么也不见了,只见红色曲臂那样奇怪地来回转动,好像原地打转,但却在走。我们跟着热气大声呼喊,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看到同伴的口型。火车过去了,我们依然跟着尾车跑,向尾车扔石头,歪戴帽子的押车员不为所动。
我们从没扔过绿皮车,看都看不够,窗口都是陌生人,他们看我们,我们也看他们,我们追着窗口跑,有人扔下东西,一包垃圾,或梨核儿,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太喜欢陌生人,远方的人,每次都追出很远,客车走了看不见了我们还在铁路上走,不知为什么。有一次走得太远,突然意外地远远发现许多黑皮车,无数平行又交叉的铁轨,闪闪光,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陌生世界。我们不知道这是车站,要是客车我们自然会想到是火车站,货车站把我们看傻了。我们猫着腰穿过铁轨,神神秘秘爬上了一列列安静的列车,从此这里是我们的乐园。我们跳进涂着沥青的车厢,进入闷罐车厢,从车尾到火车头,扳动拉杆,发出“呜,呜,呜”想象中的声音。在帽型尾车上,我们扶着简易的铁栏,站在押车人常站的地方招手,望远方,模仿叼着烟的姿势,从里面手扶门边只露半个身子,挥舞帽子。我们探寻各种可能的发现,工具箱、大衣、帽子、暖壶、杯子、饭盒、工作服,偶尔发现有工具箱没锁,打开看到里面有锤子、改锥、钳子、扳子、轴承,太让我们兴奋了。我们戴上工帽,穿上工作服,拿着扳子拧这儿拧那儿,好像工作了一样。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孩子,货车站让我们像竹子拔节一下长了一大节,我们走路都和过去有点不一样,这一点甚至从影片中也可看出:我们不再是散散漫漫,而是步履匆匆。
那天是周二,是不是全世界星期二下午都没课?还有周六,不仅如此我们那时周四下午也没课。就算上午也常有自习课。由于课本的原因尽管我们头脑简单本能不简单,那天一吃过中午饭本能就活跃起来。在大门洞外我们等了一会儿小芹,每次差不多都是小芹最后一个出来。烟色条绒上衣,烟色的猴皮筋,猴皮筋将两条烟色硬辫勒得很紧,整个看去小芹在我们之中是最接近麻雀的,干脆说就是一只鸟。五一子打了个榧子。
我们住在南城中轴线偏西,在和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琉璃厂附近,我们院在北京也是数得着的上百户大杂院。有三个门,正门旁门和后门,从前门儿进去后门儿出来要穿过迷宫似的夹道差不多就到了宣武门了。已经说不上几进几进院,院中有路,路中有院。夹道、小巷、角门、垂花门、豁口将十几个院连在一起,有的院门紧闭,常年没人,里边有树,亭子,甚至一段小河。小河好像是暗河的一段,没出院又消失了。具体到我们小院不到十户人,是这大院中最普通的小院,虽青砖漫地但房子低矮,就算正房也比别的院矮一点,据说是早年间牲口棚。
我们等小芹倒不因为小芹是女孩,我们没什么性别意识,所有人都是一个人。主要是小芹在别的方面和我们不一样,她有零花钱我们没。小芹不和父母住,从小和姥姥住我们院,小芹父母住在北京的西城社会路,是中科院的工程师,过去节假日她父母老来我们院,去了干校后来得少多了,听说最近又去了新疆。小芹有一个姐姐在内蒙插队,还有一个弟弟跟着父母,北京、五七干校、新疆到处跑。关于小芹我们也就知道这些。每月小芹都有固定的零花钱,五块钱呢,我们一年的学杂费才五块,这笔钱由姥姥掌握着,小芹因此恨死姥姥了。
我们从大院里出来,穿过门前的前青厂胡同,这是我们梦游都不会走错的胡同,前面不远过了北柳巷十字路口就是琉璃厂。我们的学校就叫琉璃厂小学,不在街面上,在小胡同内,走九道弯、小西南园、铁胳膊胡同都行。过了铁胳膊胡同是荣宝斋,荣宝斋对面是琉璃厂唯一的一座西洋建筑,四层带白廊柱,顶部刻有:一九二二年。老辈人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诞生在这楼前,但这是我们每天的必经之路已经视而不见。直到南新华街与东西琉璃厂交叉的十字路口才稍稍陌生一点:大街对我们这一些孩子永远都有些陌生。这里有两趟公共汽车,一个是十四路,一个是十五路。十四路在这里的站不叫琉璃厂叫厂甸。厂甸到永定门一共七站:厂甸、虎坊桥、虎坊路、太平桥、陶然亭、游泳池、永定门。我们无比熟悉这些站牌,倒不是因为坐车而是每次都数着站牌走着,一站一站,比坐车还熟悉这些站。
只有小芹坐过一次,坐完就后悔了。小芹在永定门等了我们好久,在桥上吃了三根冰棍,喝了两瓶汽水,差一点就坐车回头找我们。那以后小芹每次都跟我们走,但每次五一子都别有用心地鼓动小芹坐车。开始我们不太明白,后来就一块帮腔,结果终于等到小芹一句话:要坐大家一起坐。不用说,小芹请我们坐车。但五一子还有妖蛾子。小芹自然统一买票,五一子偏要把钱给他,他自己上车买。小芹给了五一子一毛,这样我们都要自己买,小芹也没说什么给了我们每人一毛。七站地七分,售票员要找三分,找回的三分说好了要还给小芹。我们都上了车,五一子最后一个,没想到车门刚要关上,五一子突然跳下车。五一子说他不坐车了,他跑着。我们立刻明白了。五一子像匹小马奔跑起来,一直在我们后面,车快他也快,车慢他也慢,有时他变得只是一小点了,但路口到了,五一子又追上来,甚至超过我们。每一分钱对我们都是宝贵的,因为就算一分钱我们兜里都没有,小芹没想到快到第四站时我们每人花了四分钱买了票,到虎坊路纷纷下车。
原标题:《宁肯小说集《城与年》推出:面对城市记忆,我有巨大的好奇和紧迫感|访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